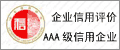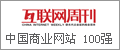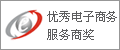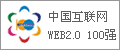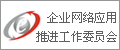“我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,比其他作家考虑得更多的肯定是它的市场表现力,它是否具有大众覆盖力。”承载尖锐的社会矛盾、反映人性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构状态?这些沉重的题材不是郭敬明的菜,他无力驾驭,也没有兴趣。他自比为商业片导演:“如果我是一个导演的话,可能就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导演,我拍的是《2012》,我要票房、要好看的视觉、要特别精彩。我不会去拍文艺片、纪录片,去反映屠杀、反映种族歧视。”
郭敬明的野心是: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赚一个“小”字。2008年出版小说《小时代1.0》的时候,他就坦率地对媒体说:“我写不了整个中国,因为我不了解,我只生活在上海,我只能记录这其中的一部分年轻人,有些是普通的大学生,有些是比较穷的年轻人,用这个小团体折射出这个时代。”
他推崇享乐主义,文字中布满浮华。在一片“带坏小孩”的指责声中,他挥霍得一如既往,往自己身上招呼各种大牌得吓人的LOGO,再拍照挂在博客上。郭敬明辩解说,这是一种为了把自己跟其他年轻人区别开来而进行的奢侈:“这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。我用这些东西,对自己今天的身份地位是一种犒赏。我觉得享乐没什么罪恶,这也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。我自己的人生当然要怎么开心怎么过,这一辈子如果赚那么多钱又不花,那还挺荒谬的。”
跟郭自己的作品一样,开放式吸收青春题材稿件的杂志《最小说》的定位也带着最浓厚的商业目的:放大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心中的轻欢浮愁,浓墨重彩地讲述与他们同龄的虚构人物悲虐的身世、情感与成长变故,佐以华丽的辞藻。
黎波把郭敬明的这种切入角度称为“主流文化里的边缘文化”:“他永远在这个区域把握得非常好。在出版创意产业,你不能不承认个人主义绝对重要性。你千万别说没有他我依然行,我就敢说,没有他你就不行!”
郭已经在更讨巧的青春市场占住了先机,并随时调整以求走得更远。2009年,借鉴日韩的轻文化读本发展模式,《最小说》随后又推出增刊《最漫画》、《最映刻》、《IWANT》,每个月分上半月刊、下半月刊分别捆绑上市,以12.8元的低价零售,主攻学生市场。
未来企业家?
危机感来袭。虽然一直在言行、打扮和心态上刻意延缓“衰老”的过程,但郭敬明确实在远离校园,而这恰恰是他最重要的目标市场。郭在2008年出版的《小时代1.0》的销量虽然相对同行来说仍有杀伤力,但已经比不上2007年时自己的纯校园题材作品《悲伤逆流成河》。
“《哈利·波特》的成功也不是J.K.罗琳个人的成功,它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团队企划案的成功,从作品的诞生到后续产品开发,美国有相关的成熟产业链足以支撑这个模式,但是在中国要完成这样是很难的,至少在目前很难。”
郭敬明很快意识到,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,巅峰也不过就是销量几百万册。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,无论是做杂志、文化出版还是实业,“吃别人的青春饭”、把个人品牌过渡到公司品牌,发展空间要比作家大得多。
上一页 下一页